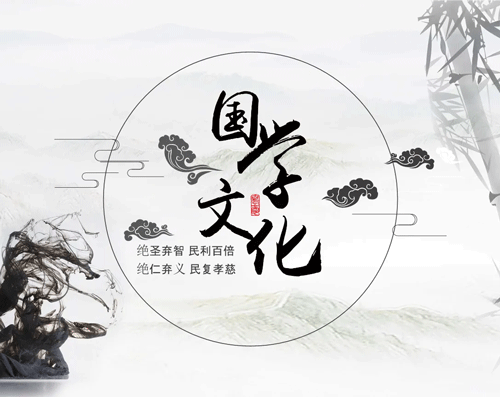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刘永明
发布时间:2023-07-19 10:20:11作者:金刚网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有数百年之久,敦煌地区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要冲,佛教在这里已经扎下了牢固的根基。从敦煌文书中可以看出,敦煌寺院林立,僧人甚多,法事活动频繁,佛教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景象。另一方面,属于中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道教在敦煌有着更为深厚的基础。大一统的唐王朝建立以后,实行文化开放、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中原文化便伴随着强大的政权力量进一步向敦煌以至更远的地区推广,道教作为三教中受到唐朝特殊青睐的本土宗教文化,推广的力度相对更大一些。所以,唐朝时期敦煌道教也达到了全盛阶段。到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两种宗教文化也在历经数百年的冲突和交流之后,渐渐走上以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发展道路。本文即以反映佛道融合内容的敦煌佛教文书(非佛经)为核心,力图揭示唐五代时期佛道融合的一些具体情状,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一、敦煌高僧与佛、道义理沟通
从敦煌文书看,敦煌高僧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对道家、道教和儒家文化多有甚深的钻研,并致力于儒、佛、道三教的融合。如后唐河西敦煌府释门法律临坛供奉大德兼通三学法师毗呢藏主沙门刘和尚(刘庆力):“释道儒流,遐迩无不悦悆”;“普丰化俗,儒道参前。”河西管内都僧统翟法荣“庄老洞赜,灵辩恒沙”;“学贯九流,声腾万里”。这些出自邈真赞的材料,虽然对传主的才学不无夸张之处,但依然明确反映了在敦煌佛教界,研习三教、三教兼通是作为名僧、高僧学识渊博精深的重要素养。应该说,这种研习和高僧长期以来致力于三教融合的文化努力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隋唐以来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和三教融合的主要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敦煌地区从事于三教融合的还有诸如管内都僧统翟法荣这样的僧界头面人物和佛学权威人士,这说明,他们的研究不仅仅是个人追求学问的行为,实际上还具有学术导向的意义;同时,这种行为对敦煌地区佛教活动的发展方向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唐后期敦煌地区曾经遭受过被吐蕃占领的特殊历史事件,道教遭受吐蕃的打击,原来留存于道观的道教经典大量流入佛教寺院,很多道经成为抄写佛经的纸张,这固然是道教的一次劫难。但同时也要看到,在长期以来三教融合的背景下,道经进入寺院,恰好有利于促进佛教人士所从事的佛、道融合行为。也许,道经流入寺院,正是吐蕃占领时期到归义军时期道经继续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敦煌文书中,有一份反映佛、道义理相融合内容的残卷,那就是S.6147《释道相通论》(拟)。该文书不见于传世文献,因而十分值得注意。可惜该文书前后均残,在仅存内容的下端文字亦有不少缺失,无法窥其全貌。从书写情况看,文书字体端正整齐,和盛唐时期的写卷相一致,所以可能是吐蕃占领敦煌之前的写卷。在这篇残存24行文字的文书片断中,引述了佛教《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涅槃经》和道家《老子》、《庄子》的内容,从义理上对佛道二教进行了沟通。这里本人根据文书中的有关书名和内容的不完全提示尽量恢复了其残缺的引文。文书内容如下:
1.故夫佛具
2.司,不登帝位,百司何处
3.但使受天命作国君,则一时
4.不研精得道,何处安一切智,未
5.者,但使降魔独悟,即一时具一
6.《维摩经》云:“始在佛树力降魔,得[甘露灭觉道成。]”(注:《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大正藏》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538页。)[《大智度]
7.论》云:“菩萨以智慧功德力[故]降魔众[已,即得阿耨多罗三]
8.藐三菩提”。(注:龙树造,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1,《大正藏》第25册,第58页。)明知种智在降
9.间智能而作。如人受生有形,则
10.情何处安。故知六情在识内受
11.中得道则用,既无假帖,六情
12.道以树叶问佛,佛即知其数者
13.耳。《大智度论》云:“菩萨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故。]
14.得作佛”。(注:《大智度论》卷20,《大正藏》第25册,第211页。)《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
15.于无为,无为无不为”。(注:《老子》第48章,《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第29页。按“无为无不为”当作“无为而无不为”。)夫“无为”者,降魔讫,“无不为”者
16.种智明,损益相乖,则道与俗反。
17.如来号种智,犹帝王号万万机,机者机应万方。种智
18.者,智周一切。机应万方者,未是积万机于方寸;智周一切者,
19.未是积种智于胸怀,并是无心之慧明。所以能如此,故能应
20.万方而无极,照一切而无穷。又如明镜悬空,鉴照万象,象
21.至则见,镜无去来,圣人用心其犹若是。故《涅槃经》云:
22.“拘那含牟尼佛时名曰法镜”。(注: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15,《大正藏》第12册,第452页。)《庄子》云:“至人[之用心若镜”,](注:《庄子·应帝王第七》:“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载《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第138页。)
23.义同一理。
24.服药养形而为(下缺)
从内容可以看出,文书的作者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援引道家老庄的无为之道诠释佛家的智慧之学。文书旁征博引,颇有甚深理趣。由于文书仅为部分残卷,所以我们无法得知这是一份出自敦煌本地人士之手的作品,还是从内地传到敦煌地区的作品。但如果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进行考察,可知这种融佛道义理于一体的作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佛教初传时期,佛教与道家道教之间便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两者既相斗争冲突,又相吸摄融合,显得极为复杂。从吸摄融合的角度看,佛教一方面在传入中土之初,就不断地借鉴、吸收包括道家道教在内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如译经时借用道家、道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名相;另一方面,不少佛经的制作本身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从S.6147《释道相通论》中看不出佛、道彼此之间的抑扬褒贬,其所显示的态度是平和公允的。它将道家无为之学与佛家无为法相提并论,以《庄子》的“至人用心若镜”解释《涅槃经》的“法镜”,以全面说明两者“义同一理”,体现出一种平心静气的、以沟通融合为目的的研究旨趣。所以本人以为,这样的作品可能就是产生于以三教融合为主要基调的中唐以前时期。至于作者无论是否为敦煌人士,其作品既然留存于敦煌地区,就能说明它与敦煌僧界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敦煌地区的佛道关系。前述敦煌僧界头面人物翟法荣“庄老洞赜”;刘庆力和尚在弘扬佛法时能够“儒道参前”,并以实际行为得到三教人士的欢迎,这说明他们对道家、道教的态度与《释道相通论》的作者所持态度是一致的,同样主张佛、道相通乃至三教融合,而且他们立足于相通融合的研究和传播均取得了“遐迩无不悦悆”的良好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地区的佛、道关系乃至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总格局是以融合为主流的(至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由外在因素带来的变化另当别论)。
由于道教将老子神化为最高教主太上老君;而唐代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以庄子为道教的真人,以《道德经》和《庄子》为“真经”。所以,这种在义理层面对佛经和道家经典《道德经》和《庄子》“义同一理”式的沟通融合,实际上也是对佛教和道教义理的沟通融合。而这种由僧界头面人物和名僧所进行的沟通融合恰恰足以为广大佛教信徒在宗教生活中融合佛、道两教的行为提供深层次的理论依据。